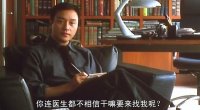羅雯麗
發表時間:2016-04-08 19:46:03
2703
0
7
羅雯麗
發表時間:2016-04-08 19:46:03
2703
0
7
十幾歲時讀過挪威的森林,卻并不能領會其意義。作者似乎有意把整個故事寫得碎片化,只從男主渡邊的眼睛觀察每一個人的行為。而整個故事,除了直子和綠子兩個貫穿得比較連貫的人物之外,只有一些不連貫的,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小故事。大部分讀者讀完了以后,除了表示這樣的生活無法理解以外,便是覺得“小日本太變態了!”
我曾經也是這樣認為的,不過年歲漸長,心理學學得越深,心理咨詢做的越多,便越來越理解作者描述的那些人物,而逐漸覺得作者簡直是個掃地僧,寥寥數筆,勾勒出若干人物,卻入木三分。這種入木三分,是一種藝術家特有的抽象化的能力。
要知道,挪威的森林在日本銷量達到800萬冊,而日本人口也就一億多而已。可見作者一定是滿足了日本民眾的某些情緒上的需求才有此銷量奇跡。我的觀點是,此書確實反映了日本社會的某些心理狀態,而且刻畫深入,才讓日本人如此上癮。
我并沒有在日本生活過,所以恐怕對日本的社會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不過在不同的國家生活體驗,與日本人的交往,以及對心理學社會學的了解,讓我能做一些推測。
日本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不管是經濟層面還是社會服務層面。一個生活在日本的人,但凡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讀書和就業,吃喝和醫療是不愁的,那么剩下的,就是需要滿足感情需求。
我有一位關系比較好的日本心理治療學學友,常常給我講日本的生活。當然,她本人是非常討厭日本的生活的,從只能睡五個小時的東京,到充滿歧視而不自知以至于對于她的有阿斯伯格綜合癥的孩子的各種不公平對待,她實在無法愛上這個國家。她說,日本是一個地震多發的國家,這造成了日本人有一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設想一下,這是一個極為憂傷的事實,所以,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可能明天就會死,或者不知道哪天就會死的時候,與自己喜歡的人發生性愛關系,將會是第一選擇。所以日本人很自然的對性愛秉持開放的態度。
日本又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儒家文化的深刻印記是,重關系,輕個體。表面和諧的關系下,個體的個人體驗被無視。如兩個本無愛的人因為婚姻必須生活在一起,而又互相有不可出軌的契約,貌合神離暗地掐架隱性出軌就是結果。于是在日本,在儒家文化之下,流淌的是一種憂傷,這種哀傷是隱性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之外,人們只能忽略這種憂傷,以生活下去。他們愿意做援交的女孩,愿意成為工作狂,愿意把性與愛分開。。。文化氛圍,使得他們必須忽略文化對于私人空間的侵犯。
當然中國與日本又不同。日本是地震與儒家思想共同作用的結果,造成日本人需要有“性”作為生活苦難的出口。中國人的出口在坑蒙拐騙和權力斗爭。。。原諒我如此直接。其實善惡永遠并行,一個看起來至善的人,必會有一個至惡的出口,一個看起來極和諧的國家,必然有一個方面極不和諧。
歐美社會往往兩面性比較小。譬如說,老友記,欲望都市,屌絲女士這樣的流行劇,基本反映的是歐美人的真實生活。人們在劇里朋友之間,會互相折磨,會憤怒,但是仍然要面對生活的種種不堪。而在中國,生活真正不堪的面目是不允許被鏡頭真實的紀錄的,老師們都溫文和藹,學生必須是上進的好學生,電視劇中的人物是無性的。有如此差距,是因為人們對當下自己的生活搬上銀幕有自卑感,認為自己的生活應該更好一些才值得搬上銀幕。
這看起來不好理解,其實也不難,正常人的生活里,性和憤怒暴力其實是重要內容。老友記里,好朋友之間也會互相攻擊,但是攻擊完了仍然是好朋友,是一種現實常態。欲望都市里,幾位姑娘的生活就是以性愛交友為主體,是以性為主體的。這是比較真實的生活。如果人們不能接受自己身上這兩個部分,便只能拍宮廷劇,偶像劇,手撕鬼子劇。宮廷劇和武俠劇都是無性的,但是可以滿足人們對暴力的渴望,卻是一個遠在天邊的社會,可以與自己有關,也可以與自己無關。偶像劇則多完全回避了人性中的暴力,將人性一分為二,只取善的一面。
日本社會終究與中國社會不同,所以有些問題是可以談的,所以盡管日本人的社會生活與真實的生活不完全一致,但是并不妨礙文學作品的現實性,所以,便有了挪威的森林這種抽象主義的現實小說。
談完了背景,要正式談小說了。
直子與木月都是無法與外界達成正常溝通的一對戀人,而男主人公渡邊是一個正常的,可以與外界正常溝通的人。
直子與木月自小一起長大,其實他們之間的關系,與其說是情侶,不如說是兄妹更為貼切,他們因為太熟悉對方而無法對彼此產生情侶間應有的性欲。而他們的感情,并不是因為他們深愛對方,而是因為他們無法離開對方,他們無法離開對方的原因是,他們無法與外界達成正常的溝通。
所以他們需要渡邊這樣一個與外界連接的橋梁,其實他們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不然不會如此明確的邀請渡邊加入他們的生活。
如何看出直子與木月無法達成正常溝通呢?直子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她總是以歡笑面示人,以至于每隔一段時間,她需要把自己關在屋子里抑郁三五天。這是抑郁癥的典型癥狀,而這種抑郁癥,在她畢業以后的工作中越來越嚴重的控制她,因為工作中對人際的要求比在大學中要高得多。要求自己以笑面示人,是一種強迫性思維,多起源于父母對于這樣的孩子要求非常高,不接受孩子本身的自然的一面,儒家文化的教育的確有這種傾向,所以如此教養的孩子自小就學會戴面具生活,以至于成年以后雖然飽經痛苦,仍然無法取下面具。直子非常符合儒家對人的期待——安靜,乖巧,可愛,看起來如小白兔一般無害。這也是日本影視作品中女性最常見的形象。
渡邊并沒有描述過多木月是一個怎樣的人,不過木月是三人在一起的時候幽默而健談的,他并不想把這種健談顯示給別人,也就是說,木月是先發現自己的面具的,他因此而不想取悅別人。于是先于直子自殺了。
很遺憾盡管直子經歷了精神病醫院的治療,仍然選擇了死亡。
直子在精神病醫院的治療是無效的,因為這并沒有幫助她了解到自己存在的真正價值是不需要取悅別人的。這一點,從她與渡邊在精神病醫院時,她試圖為渡邊手炮看出,她以為這樣子可以讓渡邊覺得被重視,被取悅,可是在我看來,這卻徹底暴露了她這一生的悲劇——她從來就沒有了解過人性。她從來就不知道渡邊要的是什么,她以為這就是渡邊想要的。
日本社會還有一個致命傷,就是女性的地位問題。女性地位以國家為單位的排名中,日本僅好于土耳其,落后中國許多。女性無地位,導致她們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取悅男性,哦不對,她們不明白男性并不需要被取悅,她們應當取悅自己。唉,女性被嚴重物化的文化中,女性本來就被視為工具和物品,如此,女性如何又能知道如何取悅自己呢?
木月并不是真的愛直子,否則也不會輕易的撒手而去,這其實是直子真正耿耿于懷的,也是直子最終領悟到的,恐怕也是直子最終的死因,因為她終于明白了她唯一愛的人并不愛她。直子與木月在一起,我想,是一種彬彬有禮的陪伴,并不是發自內心激情迸發的愛情。他們在一起純屬無奈,因為他們都無法與外界產生真正的聯系。被迫在一起的感情是愛嗎?如果再經歷三十年的生活,他們或許會明白這就是愛,可是對于十多歲的少男少女,這就是悲劇。
至于女鋼琴教師玲子,她是一個令人同情的精神病患者。她是一個受害者,害她的,是那個善于編織謊言的勾引她的十三歲同性戀小女孩,社會輿論和無視她受傷的事實的丈夫,但是最終近精神病醫院的,卻是玲子這樣正常的人。
不過說玲子正常,也并非完全見得。玲子的痛苦在于,她無法完全的接受這個世界上有善就有惡的事實。那勾引她的女孩,便是這世上至惡的代表——縱情欲,愛同性,甚至不惜顛倒黑白。可是坦白說來,如此之至惡,非佛陀難以承受,普通人如你我,恐怕都要發瘋,所以,進入精神病醫院,反而成了她最佳的庇護。整個社會加諸于個人身上的悲劇,令人扼腕嘆息。
綠子和渡邊是這本書里唯一的正常人。我少年時讀到綠子連續三個月只穿一個內衣感到不可思議——作者瘋了嗎?其實綠子是一個在這個社會能夠生存下去的女孩,因為她愿意為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付出,一點都不矯情,哪怕三個月只穿一件內衣。
綠子會大聲的談論女校燒衛生巾——綠子并不介意社會的看法。世人都認為衛生巾是污穢之物,中國人談論之也多加隱晦。我自小就非常不解,為何人們見到女子月經染了衣褲就一副“哎呀,天啦,你捅破了天啦”的表情。要知道,月經是這個世界上一半的人注定要有的東西,有什么不干凈的?而綠子談論的這捅破天的事情的時候完全是一臉驚訝的樣子,好像說,“哇塞,食堂里每天倒掉那么多的飯,簡直可以喂飽100只狗。”就因為這兩點,就可以知道綠子是一個率真可愛的女孩。
渡邊是一個有愛的能力的人。他能夠好好的愛直子,清楚的知道那些與他一夜情的姑娘并非他之愛,可是仍然愿意花時間陪她們。他自然也知道永澤教會他的那種,“有機會就要與姑娘在一起,不然多可惜”的生活并非他所追求的。最后能與綠子在一起,我想也是眾望所歸。
最后那個永澤,我想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本地震死亡威脅下,以性愛為發泄出口的代表性人物。這樣的生活看似美妙,實則虛無。他以為自己能操控一切,實際上內心蒼涼如老叟。我想,是他這樣的冷漠,直接導致了初美的自殺。身為儒教社會中受良好教養的女子,初美非常難逃脫那種以男性為中心的愛慕,因為她心中無自我意識,她始終需要依附男人,即使她接受良好的教育,即使她有工作,即使這個男人自私冷漠到渣,對于初美這樣的女子來說只要是愛了,便不回頭。又或許,初美是想回頭的,但是回了頭依然無法找到活著的意義,于是便自殺了。
最后的最后,對于村上村樹在書里反復提到的“以前以為生和死是對立的,后來發現死是生的一部分”對也不對,死和生確實不是對立的,不過其實生是死的一部分。這樣想的話,死,便不再是那樣可怖的面孔了。
溫馨提示:文章、帖子、評語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 給力心理
給力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