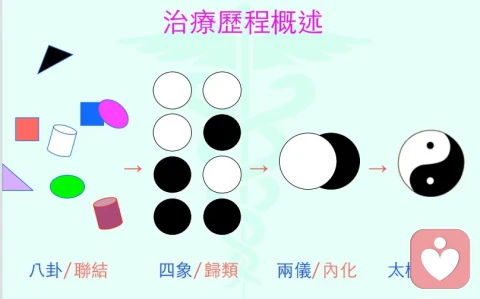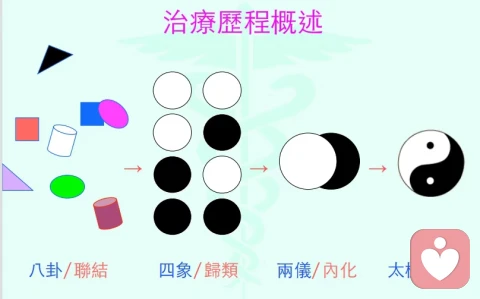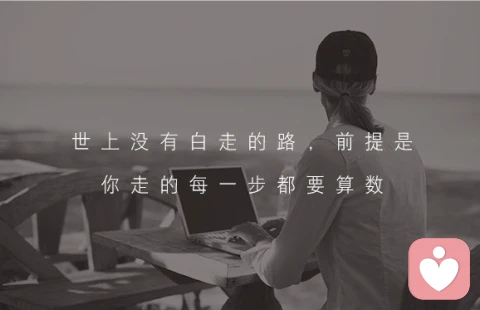在參加清華大學(xué)與幸福公益基金發(fā)起的心理熱線工作和培訓(xùn)期間,樊富珉教授特意提到三個(gè)概念:創(chuàng)傷應(yīng)激障礙(PTSD)、創(chuàng)傷應(yīng)激反應(yīng)(PTR)和創(chuàng)傷應(yīng)激后成長(zhǎng)(PTG: posttrauma growth)。PTSD不等于PTR或PTG。PTSD是最嚴(yán)重的那一等級(jí),需要接受心理咨詢或治療,而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是可以從危機(jī)事件中得到成長(zhǎng)的。
她提到中科院心理所的一項(xiàng)研究發(fā)現(xiàn):遇到創(chuàng)傷危機(jī)時(shí),大約有30%左右的人有良好的自愈能力(PTG),有60%左右的人處于中等恢復(fù)能力。只有15%左右缺乏心理彈性的人才需要危機(jī)干預(yù)和救援。
關(guān)于創(chuàng)傷
客體關(guān)系流派大師溫尼科特說(shuō)過(guò)"沒(méi)有人不帶著創(chuàng)傷長(zhǎng)大,因?yàn)闆](méi)有父母是完美的。" 幼年被養(yǎng)育、對(duì)待的方式影響著成年后我們面對(duì)矛盾、沖突和危機(jī)時(shí)的應(yīng)對(duì)方式。我們每個(gè)人都是生活的參與者,或早或晚都會(huì)遭遇生命中的至暗時(shí)刻。當(dāng)遇到巨大挫折時(shí),小孩子可以肆意表達(dá)自己的喜怒哀樂(lè),而成年人卻不得不學(xué)會(huì)控制和內(nèi)化。
今天想分享的這本書(shū)《身體從未忘記》是一本關(guān)于創(chuàng)傷療愈的書(shū),也是在督導(dǎo)時(shí)仇劍鎣教授推薦的,很多從事心理治療的老師也常有分享。它代表當(dāng)今心理創(chuàng)傷療愈的一個(gè)新的方向:藥物治療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副作用,單純地依賴藥物是不可取的。與他人鏈接,重建社會(huì)關(guān)系是重要的支持資源。
通常來(lái)說(shuō),當(dāng)人生發(fā)生天災(zāi)人禍后,普通人都會(huì)經(jīng)歷一個(gè)從沖擊否認(rèn)—憤怒悲傷—接受現(xiàn)實(shí)—重建生活秩序的過(guò)程。大多人半年后都可以慢慢恢復(fù)。也有一部分的悲傷是凍結(jié)、延后的。所以梁曉聲會(huì)說(shuō),"喪親悲傷是在失去親人很久后,思念和傷痛在看到一切和亡者相關(guān)的事物才開(kāi)始浮現(xiàn)。" 那時(shí)候才是思念、悲傷開(kāi)始蔓延的階段。而這一類當(dāng)時(shí)通過(guò)記憶屏蔽,不能及時(shí)清理創(chuàng)傷的人,反而會(huì)遲遲走不出創(chuàng)傷。
以下為轉(zhuǎn)載內(nèi)容:
主流醫(yī)學(xué)堅(jiān)定不移地認(rèn)為,只有通過(guò)化學(xué)物質(zhì)才能夠保證我們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zhì),但事實(shí)上,除了藥物,還有很多方式可以達(dá)成我們身體健康和體內(nèi)的化學(xué)平衡,但這些方式幾乎沒(méi)有被考慮過(guò)。大腦-疾病模型忽視了以下事實(shí):
①人與人之間既可以互相毀滅,也可以互相拯救:恢復(fù)社會(huì)關(guān)系是康復(fù)的中心;
②語(yǔ)言給予我們改變自我和他人的力量,通過(guò)敘述經(jīng)歷,我們得以了解自我和世界的意義;
③我們可以調(diào)節(jié)我們的生理狀況,包括可以通過(guò)簡(jiǎn)單的呼吸、動(dòng)作和觸摸調(diào)節(jié)我們身體和大腦的自主運(yùn)動(dòng);
④我們可以改變社會(huì)狀態(tài),創(chuàng)造一個(gè)大人小孩都能感到安全和蓬勃發(fā)展的環(huán)境。
如果我們忽視這些人性的基本維度,我們就剝奪了人們愈合創(chuàng)傷、恢復(fù)自主的能力。作為一個(gè)病人,而不是一個(gè)療愈過(guò)程的參與者,其實(shí)是在將這些受苦的人與他們的環(huán)境隔絕,將他們的內(nèi)在異化。考慮到藥物的局限性,我開(kāi)始思考,是否可以找到一種更為自然的方式,幫助人們應(yīng)對(duì)創(chuàng)傷后的應(yīng)激狀態(tài)。
911目擊者5歲的小男孩諾姆,24個(gè)小時(shí)就能用他的想象力處理他目睹的悲劇,從而繼續(xù)生活。諾姆很幸運(yùn)。他的整個(gè)家庭都毫發(fā)無(wú)傷,他得以在一個(gè)充滿愛(ài)的家庭環(huán)境中成長(zhǎng),因此,他能夠理解,他所目睹的災(zāi)難已經(jīng)過(guò)去。孩子應(yīng)對(duì)災(zāi)難的方式通常取決于他們的父母。只要他們的養(yǎng)育者仍然保持平靜鎮(zhèn)定,回應(yīng)孩子的需求,那么,即使孩子們經(jīng)歷過(guò)可怕的事情,也能夠健康地成長(zhǎng)。
諾姆的經(jīng)歷反映了兩項(xiàng)對(duì)于人類幸存而言至關(guān)重要的適應(yīng)性技能:在災(zāi)難發(fā)生的時(shí)候,諾姆用積極的行動(dòng)逃離災(zāi)難,他得以自我拯救;另外,他一回到安全的家中,大腦和身體的警報(bào)就平息了,這讓他平靜下來(lái),理解剛剛發(fā)生的災(zāi)難,甚至能用想象(例如一個(gè)救生用的蹦床)替代他目睹的場(chǎng)景。
與諾姆相反,受創(chuàng)傷的人卡在他們的經(jīng)歷中,因?yàn)樗麄儾荒軐⑿碌慕?jīng)驗(yàn)整合到他們的生活中。我在圣誕節(jié)收到巴頓將軍麾下的退伍士兵送我的手表時(shí),我很感動(dòng),但這也是個(gè)悲傷的象征,這實(shí)際上意味著他們的生命停頓在1944年。受創(chuàng)傷意味著你將圍繞著創(chuàng)傷組織日常生活,你所有新遇見(jiàn)的人和事都無(wú)可避免地沾染上舊日的創(chuàng)傷回憶。
創(chuàng)傷過(guò)后,人們似乎通過(guò)另一個(gè)神經(jīng)系統(tǒng)來(lái)觀察世界:幸存者將全副精力傾注在抑制他們內(nèi)心的混亂中,忽視了他們實(shí)際的生活。他們?cè)噲D保持正常、抑制一切不堪忍受的生理狀況。他們的這些努力很可能引發(fā)一系列生理問(wèn)題,例如纖維肌痛、慢性疲勞和其他免疫系統(tǒng)疾病。這就是為什么對(duì)于創(chuàng)傷的治療需要牽涉一系列的器官、軀體、思維和大腦。
——節(jié)選自《身體從未忘記》